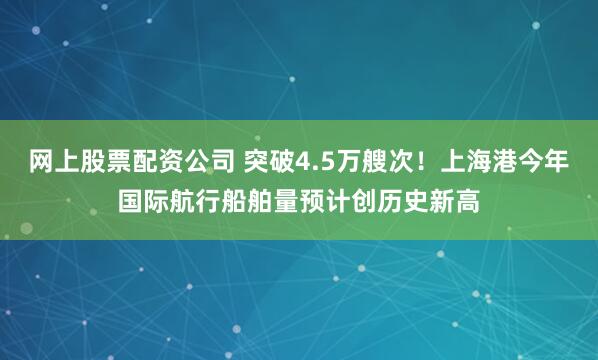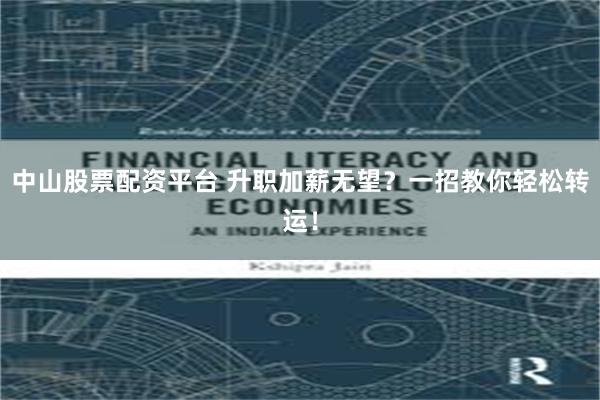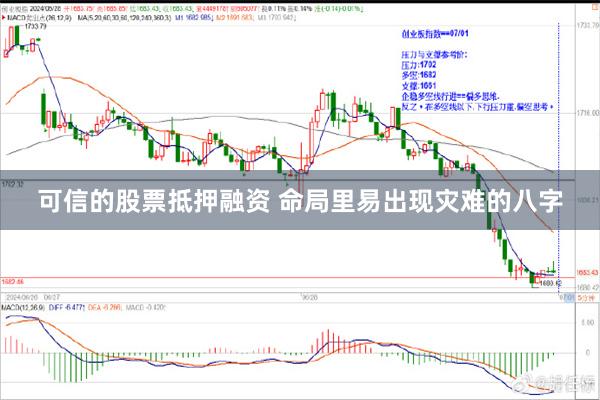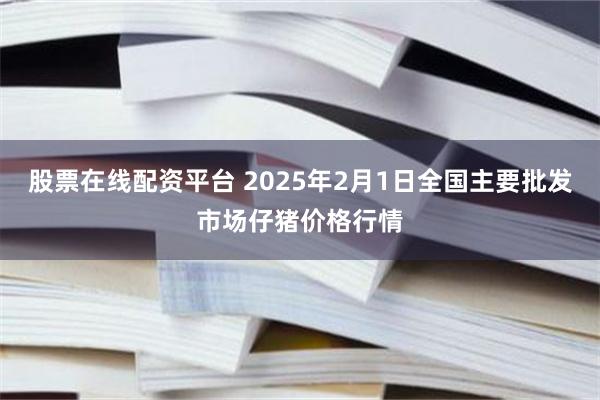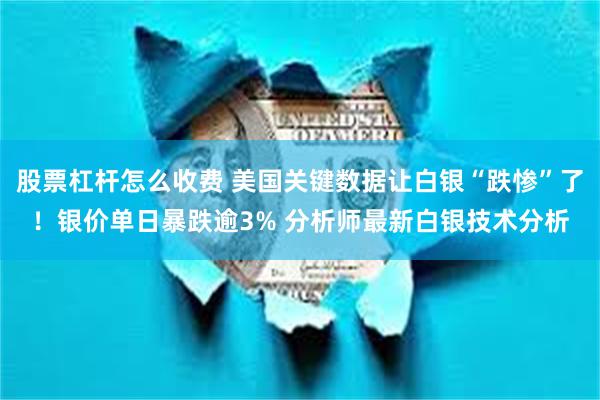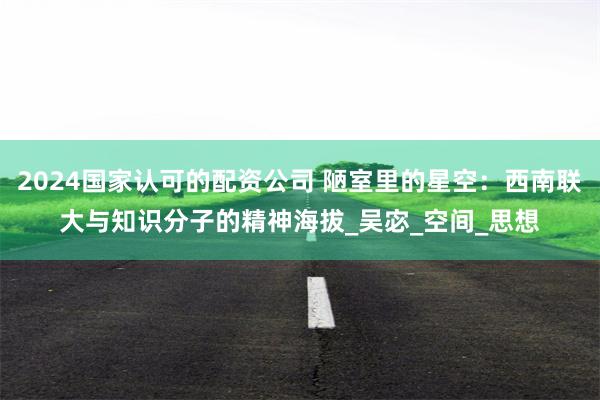
钱穆、闻一多、吴宓、沈有鼎四人挤在一间陋室里的场景,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富象征意义的画面:一盏小灯下,闻一多研读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剪影;吴宓用红笔严谨勾勒教案的侧影;沈有鼎对"良夜"的感叹与钱穆静默的观察——这间陋室恰如一个微缩的宇宙2024国家认可的配资公司,映照着整个西南联大的精神世界。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师生踏上漫长南迁之路。这场迁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,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之际的一次精神长征。当这群中国最杰出的学者被迫离开精心建造的实验室、图书馆,蜗居在铁皮屋顶的教室和谷仓改造的宿舍时,他们携带的不是细软家当,而是更为珍贵的精神火种。梅贻琦"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"的名言,在这场迁徙中获得了最为悲壮的诠释。
展开剩余63%西南联大的"陋室"呈现出惊人的精神密度。华罗庚在两间小厢楼里完成《堆垒素数论》的写作,牛擦墙、猪马同圈的嘈杂声中,他的数学思维却达到了惊人的高度;金岳霖在唐家花园戏楼的包厢角落里,完成了《论道》等重要著作;冯友兰在油灯下写出《新理学》。这些陋室中的学术成果,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基石。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精神的极度丰盈形成鲜明对比,这种反差恰恰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海拔——他们能够在物理空间的压缩中实现思想空间的无限拓展。
更为动人的是这些陋室中生长出的精神共同体。吴宓对沈有鼎的"申斥"表面上是责备,实则是学术共同体对各自精神空间的相互尊重;金岳霖获得的那方"领地",是同仁们对纯粹思考的集体守护;楼上楼下关于扫地的喊话,将日常琐事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幽默与体谅。这些细节表明,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仅在忍受艰苦,更在主动构建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——在战火纷飞中保持知识分子的尊严与温度。
西南联大的陋室精神对当代高等教育构成了深刻的启示。在当今大学竞相建造高楼大厦的背景下,我们是否遗失了更为珍贵的精神追求?当学术评价日益量化,我们是否还能守护那片纯粹思考的"领地"?西南联大告诉我们,教育的本质不在于硬件的豪华,而在于能否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无限的思想可能。那些铁皮屋顶下诞生的思想,远比许多现代玻璃幕墙大楼里的成果更为不朽。
陋室里的星空之所以明亮,是因为它映照的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精神坚守。八十多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回望那些拥挤的宿舍、油灯下的身影、幽默的喊话时2024国家认可的配资公司,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,更是一种可能——在最艰难的环境中,人依然可以保持思想的尊严与高度。西南联大的故事提醒我们:真正的教育不在于传授具体知识,而在于培养一种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能力。这种能力,或许是我们从那些陋室中继承的最宝贵遗产。
发布于:天津市